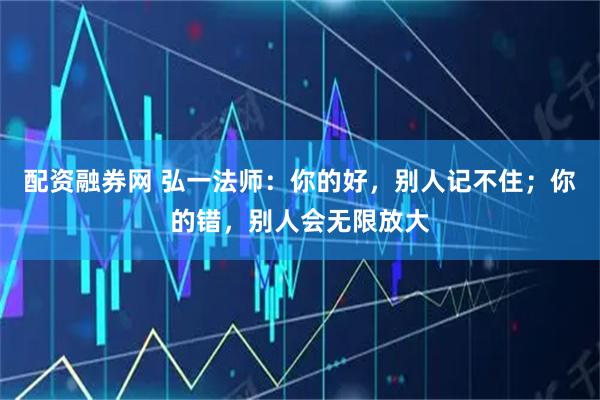潮新闻客户端 郭楠配资炒股官网开户
9月20日下午,浙江文学馆“文心大讲堂”第4期在一楼多功能厅隆重举行。当代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得主、安徽省文联主席、安徽省作协主席陈先发携新诗集《碧水深涡》,以“汉诗十讲”为主题,带来一场融理论深度、创作经验与时代关怀于一体的文学和思想盛宴。
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院(馆)长程士庆在欢迎辞中,分享了他与陈先发的往日“复旦擦肩之缘”,并提到陈先发不仅是当代一位重要的诗人,还曾是新华社资深记者,深入一线完成过多篇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报道,多重的社会身份培植了陈先发更具厚度的文学生命。
活动现场,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得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沈苇,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院(馆)长程士庆上台,接受了陈先发捐赠的《碧水深涡》《写碑之心》《九章》等十余部代表作,这些作品将纳入浙江文学馆馆藏。
展开剩余89%陈先发的讲座以“汉诗十讲”为框架,系统阐述了他对诗歌创作与精神建设的思考,节选部分讲座内容以飨读者:
一、每个人都活在生命的有限性之中,诗是一种面向“超我”的饥渴
生而为人的本质特征,正是“有限”二字,以生不满百年之躯,在日常生存的琐屑中陷于“两个我”相冲突的挣扎:外在的、在各种欲望中纠缠的、每日奔波的“外我”之中,都面临“内我”建设的强烈渴望;诗歌正是以语言创新来构建这个“内在自我”的通道。诗歌本质上是对“超我”的一种饥渴——我们渴望在诗的写作或阅读超越生存的有限性,令一己之内的内在生命更为丰沛与鲜活。
二、诗要触碰无穷的他人之心,期待当代汉诗在“觉他性”的恢复中打通与时代与他人的内在链接
诗人重视个体生命经验表达并形成丰富而多元的诗学生态,这当然是好事,但同时,诗的“觉他能力”在衰减,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许多诗人对普遍性、公共现象的研究,丧失了热情,对个体语言劳动之外和“圈子”之外的公共事件关注少,或者说难以形成有穿透力和前瞻性的认知。对大面积的社会生态之变,对人的异化,无法形成有效的思考能力。本质上,这是一种能力缺失。一个巨变的时代向每个精神领域都会发出强大的追问,而有愿望、有能力回应这种追问的诗人太少了。这当然是诗歌生命力逐渐萎缩的一个原因。杜甫以“吾庐独破”去链接天下寒士,期待当代诗歌作为整体性文化力量恢复并强化与社会、与他人、与时代事件之间深刻的对话关系。
三、好的诗人当有清晰的历史意识并以其作品整体来建设“抵达深处的精神结构”
没有一个诗人可以回避与他所处时代的对话关系,有清晰的历史意识,才能更理性地捕捉本时代最为本质的特点。好的诗人可以在开阔的历史视野中,让具体、细碎之物开口说话,说出本时代特有的语调与声音。一个好的诗人,一生作品从整体上,一定要有个“能抵达时间深处的精神结构”。正如《白鹿原》以对应了中国两千多年宗族体制破产这一历史主题而达到它精神层面巨大价值一样,一个好诗人要善于从生存事物中捕捉历史的声音,筑构他自己的“精神结构”。
四、找到你“独一无二的语调”
语调的个人性,是诗中具体而珍贵的东西。一个诗人留给后世的,往往就是他“独一无二的语调”——哪怕把名字隐去,依然能一眼被认出。谁也不会把李白错认为王维。“语调”关乎语言观、风格化、整体气质,以及对世界的态度。独特的形式感,是语调的一种。没有独特语调,就没有诗的生命。在写一首具体的诗之前,你没找到自己的语调,就可以不写。诗人价值的一个显在标志,就是语调的不可复制性。年轻诗人尤其要注意摆脱“强力诗人”的语调影响,慢慢形成自己的声息。一旦形成了自己的语调,就要不断强化它——在诗的多变中要努力保持个人语调的独特性,令其成为一种标识物。
五、在“穷尽一隅”中建设个人符号系统
重要的作家和诗人会建成一个个体符号系统,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划言的高密东北乡,数不胜数。几乎是作家的“第二自我”。符号的丰富性并不在多,而在真正地穷尽一隅。福克纳说过:“在邮票大小的地方写作。”符号的个人性,正是一个人独到生命经验的寄托,是你精神世界的“锚点”。找到这个精神锚点,长久地呆在里面,直到这个一隅形成与你生命逐步一致的呼吸。我的随笔集《黑池坝笔记》今年内要出第三卷,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生命抽屉”,我个人的声音都存放在其中。
六、一个人体内的“读与写的深刻互动”:以声音赋予汉字以生命
茨维塔耶娃曾被称为“用声音写诗的诗人”,而声音在汉语上的表现力,我想可能超过世上其它语言。诗之中“歌”的特质。一个诗人要写一首诗时,一定要反复去读它,让声音与文字的形体一起形成“意义的合体”。声音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与诗歌的情感、意义匹配中有太多的微妙之处,需要用心把握。文字读的声音,是这首诗“内在声音”的来源之一。在何处隔开、何处断裂、在何处用什么样的符号,声音有自己的发言权。诗所创造的另一种奇迹是,它让你听见的声音,根本不来源于耳膜。你的每一个毛孔、每一组细胞、每一根脑神经都有倾听的能力。你能目睹自身的“听见”。从写作的角度,一个诗人如果不想控制自己诗内的声音体系,不想让诗中的声音形成坡度、曲面、丘壑,他无疑是麻木的。甚至可以声音是诗歌的“血液”——没有内在声音的参与,诗歌就是没有生命的空躯壳。
七、重视语态的丰富性训练,同时多文体写作中获得启示
譬如,我很难喜欢上一首二十行以上却全部是陈述句的诗。语句、语态的丰富性,是一首诗生命力的一部分。诗的“态”,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配合一首诗内在需要的、生动多变的句式,是柔韧有力的肢体。语态的起伏多变,会强化诗的细节表现力。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我觉得一个诗人要尽量多地进行多文体写作,长篇小说会强化你的结构能力和内在视野构造能力,散文随笔等等,都可能从不同维度有益于诗的创造,努力在此处强化文体强力,同样道理,尤其对一个青年诗人,你的阅读也应尽量保持开放性,我的书架上,诗集占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五。
八、“人物形象的深度缺失”是一大遗憾
我经常想到惠特曼笔下博杂、有力、充溢着生命野性的人物形象,屠夫酒徒、黑奴囚犯,妓女伤兵等等。布考斯基诗中的恶棍与流浪汉、做苦役的长工与一无所依的昏聩老人等等。当然还有白居易笔下的商人妇与卖炭翁,老杜笔下“夜捉人”的石壕吏与哭哭啼啼的老妇人……人的生态与诗最核心的力量,当代汉诗没有特别有冲击力与符号深度的人物形象,是个显见的遗憾。人的悲合离合,人的命运变迁,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世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成的,可供介入的景象与这些景象所蕴籍的深度与强度,都是特别值得珍视的写作资源,再过些年,这方面的记忆会淡漠仍至空空耗尽,期待这方面出现不凡的力作,其实,理应出现。
九、对语言创新要怀有足够强烈的冲动
一个时代的语言是否僵化,是否失去活力,诗歌与诗人承担着使命。我一直认为,诗的力量来源,或者说,所有艺术的来源无非是三方面:永不枯竭地探索自我的热情、不可遏止的对他人苦难的怜悯、足够强烈地更新语言(或其它艺术符号)的冲动。诗人必须为创新更新语言系统作出努力。要敢于“造词”,敢于创新表达。我十八岁写的第一首诗里,我想活在一个儒侠并举的中国。“儒侠并举”这个词,就是我自己造的。“写碑之心”“渐老如匕”“弱鸟有食”等等,我造了不少词。倒不是为了刻意地标新立异,而是当一首诗内部某种氛围出现时,找不到一个现成的词来表达,不得不去造一个出来。修辞的创新、语言向自身索取动力的机制,都是神秘的,时而全然不为作者所控。总有一些词、一些段落仿佛是墨水中自动涌出的,是超越性的力量在浑然不觉中到来。仿似我们勤苦的、意志明确的写作只是等待、预备,只是伏地埋首的迎接。而它的到来,依然是一种意外。没有了这危险的意外,写作又将寡味几许?
十、关于风格化与“个性的消逝”,诗期待时代旷野中的声音
谈了这么多,这个话题是个矛盾的话题,前面讲了许多有关风格化、个人符号与独特语调的想法,最后我得讲讲貌似与这些冲突但到了我这年龄不得不去面对的另一端的话题。诗人的自我要融入到人类共同经验中。济慈说过:一个重要的诗人,他身上的‘我’应该消失。我的理解是,要以“所有人”为其“第二自我”。艾略特说,诗不是在表现个性,而是在逃避个性。他多次谈到个人性的消解问题。这些怎么理解?一个理想的境界或许是,出现在时代旷野中一种诗的声音,是谁的声音已然不重要,关键是它是否时代最为本质的声音,真正留下了时代印记的声音,真正超越了个体的普遍之声。风格化是外在的壳的风貌,而个性的消逝更多意味着诗要摆脱囿于一己的所有束缚,为心灵的普遍性发声。我前不久在另一访谈中说过这么一段:一种成熟的超越模式,是让诗进入匿名状态。无姓无名的,神思与远道。就像诗经与汉乐府中那些诗人一样。作者的隐匿或逃遁,让诗在人群中获得最自由的呼吸。这里有个基本假设:在无数的他者体内,可以建立起“诸我”的连接,诗与无数的他人获得内心的连接。诗应当到更广漠的人群中去呼吸,而不是仅仅与同类特质的人形成呼应。如果只在特定界域内才有活力,诗貌似寻到了知音,实则是深刻的不幸。诗应去更抗拒它的人群中,在完全不能预测的时空中,在麻木与艰难中活下去。这才是诗的精神,或者说是一个诗人心中“超我”的来临。
在提问环节,观众就“造词的边界”“诗歌中‘来源于生活’与‘高于生活’的平衡”“诗歌中的复活与重生主题”等提问,问答十分精彩:
【文学爱好者】:陈老师您好!我刚才听您提到“造词”,特别有感触。我自己写诗的时候,也尝试过创造一些新词,但很多人说这些词“不规范”“不被认可”,感觉很难坚持。想请教您,我们在造词的时候,应该如何把握“创新”和“规范”的平衡?如果造的词不被认可,还要继续坚持吗?
【陈先发】:很多诗人会遇到这个困惑。首先,我讲的“造词”的核心意思,是切合这首诗内在氛围的语言创新,不是“刻意而造”。诗在写作进程会向作者表达一种渴望,——已经成形的所有东西,已经固化的表达再无法精确传达感受力之时,造几个词又何妨?所谓“规范”和“创新”的平衡,关键在于“语境”——一个新词,在特定的语境里是必须的,合理的。不被接受也不必在意。词有词的命运,或许后世,它突然就有新的生命了。诗人的语言“探索”——当然远不仅是造词,哪怕失败了,也能为后来的诗人提供经验。写作要有“做失败者”的勇气,这是诗人对语言的责任,也是对自己内心的忠实。
【青年诗人敖运涛】:陈老师您好!我特别喜欢您的《理想国》《丹青见》这些诗,感觉这些诗“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既贴近现实,又有很深的哲理,不同层次的读者能读出不同的深度。想请教您,我们在写作时,应该如何把握“生活”和“哲理”的平衡?怎么才能让诗既有“烟火”,又有“高度”?
【陈先发】:谢谢喜欢这首《理想国》。诗中“小鸟啄击玻璃”是真实发生的事件,现在仍然在持续。我的书房有一扇落地窗,对着院子,每天都有小鸟来猛烈啄击玻璃,我一开始非常纳闷,后来走到玻璃的另一侧,才恍然大悟,院中的树冠树荫映在玻璃中,远比真实的树更美更具视觉的诱惑,小鸟误以为是“绿色的天堂”,想击破障碍飞进去。想想人类命运,历史关于理想国的种种愿望,何偿不是如此?我们难道不是这些看上去愚而弱的小鸟?我们观看历史,有时候正好走到“另一侧”!在这一刻,小鸟与人的命运、甚至与历史在一个非常微小的动作中,打通了。我们甚至会从小鸟上怜悯起人类自身。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哲理,其实无所谓要去发掘什么道理,我只是在描述这个景象,越具体越清晰,你可能就越如临现场,是你的“见”触动了你的“思”,我在写作时并不想把这些道理交到你手上。作者在诗中的“强加”与过度注入,在我看来,是一种毛病。
【青年诗人萧楚天】:陈老师您好!我很多年前第一次读您的《前世》,就是写梁祝的那首诗,就被深深震撼了,后来我自己写诗,也经常会写“前世”“来生”“轮回”这样的主题。今天听您说“诗歌是对超我的饥渴,是对有限性的超越”,突然对这些主题有了新的理解。这两天我也在集中读您的新诗集《碧水深涡》,从题目就能感受到您对有限性的超越,对无限性的探索,“深涡”像一个黑洞一样的无尽漩涡,却能通过语言激发出很多思考的空间。想请教您,您如何看待“复活”“重生”这个主题?有限的人如何向无限的宇宙寻找精神上或感受上的复活力量?我在《碧水深涡》350页看到您写的《枯》系列,里面有句“我对一切重生皆无偏见,但无法确定灵魂这只昔日的笼中之鸟,今日是否仍在眼中”,想请您结合这个主题聊聊。
【陈先发】:这个问题触碰到了诗歌的核心要义。我理解的“复活”“重生”,不是宗教或风俗意义上的“转世”,而是精神层面的“突破性延续”,诗歌通过文字,将一种力量突破个体局限,融汇到更广阔的时空里。苏轼死于1101年,他死了吗?我读赤壁赋,宛如他在一旁对话,他的滋养历千古而如新。诗的生命,正如马斯克所说的,“死亡可能是一种幻相”。从量子纠缠的角度看,人的意志力是永恒之物——诗歌所传递的最核心力量,正是人的意志力与创造精神。诗人的情感与生命经验转化成文字,一代代被阅读、甚至被误读,不断被注入不同时空中的意义赋予,这才是真正的“重生”。
……
陈先发老师透露,本次讲座内容将整理成文并刊发。“诗歌不是密室的封闭式游戏,而是旷野中无名心灵之召唤。”本次“文心大讲堂”不仅是一场诗学讲座,更是一次对当代文学精神路径的深刻勘探。
本次讲座由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院(馆)委会成员、创研宣教部主任卢山主持配资炒股官网开户,来自浙江和杭州的诗人、作家邱建国、阿波、江离、艾璞、徐静、徐忠友、胡骁楠、徐飞、章雪霏、李未、宋云开、伍元之等80余人参加活动。
发布于:浙江省倍选网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