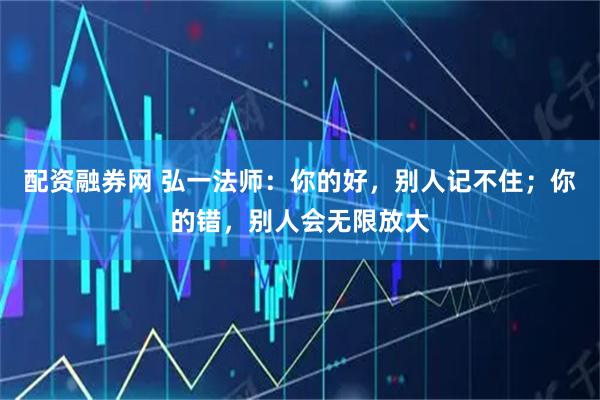《——【·前言·】——》配资老牌炒股配资门户
公孙胜没有投降,也没有战死沙场。他在梁山最风光的时候悄然离去,在战火连绵时不曾露面,在清算开始前彻底消失。
没有留下言语,没有写信告别。只在一个无人关注的时刻提出辞行,再没回来。《水浒传》写他“以终天年”,只这一句,几百号兄弟里,他成了唯一一个干干净净收场的人。
入云龙下山,入局不深却卷入风暴梁山还未坐满一百单八将,晁盖刚聚起几位义士时,就有人提到一个名字。这个人不在江湖,不是绿林头领,不是官军降将。他是个道士,道号“一清道人”,自号“入云龙”,住在蓟州二仙山。此人不是江湖草莽出身,也不是军旅出身,早年随罗真人修道,精通五雷正法。他不是用刀剑征战,而是靠符箓斗阵。
展开剩余89%晁盖一行人劫了生辰纲,遭官府追缉,避入梁山前,先找他助阵。他下山相助,不言利,不索报,背一口七星剑,一只布囊,随行入局。战后上梁山,与晁盖吴用同列,在忠义堂排第四位。一个道士居此高位,不因拳脚,不靠威望,全靠本事。此人出阵从不拖泥带水,一旦亮相,多是关键战事。
他到梁山的时机不早不晚。宋江还未正式掌权,晁盖正值权盛。梁山初成,他是策士之一,却极少干预军政。吴用负责排兵布阵,林冲秦明负责带兵打仗,公孙胜只在战阵需法术时才出手。他不主事、不参政、不干预排位,也不主动索战。只要战场需要,他便一击即退。
梁山初次对阵朝廷名将高廉时,正是他出面破阵。高廉使妖术,雷火风霜俱下,普通兵将无力接近。他取五雷符,设天罡阵,于阵中口诵咒语,火雷自天而落,高廉之术破。战后退回后军,不求功劳。那次大战,是他在梁山最大规模的初次显现。
其后数战,公孙胜多次以雷火破敌。乔道清、鄯善国师皆以妖法布阵,宋江兵马久攻不下。公孙胜数次临阵,不言兵略,不调兵,仅以法术破敌,敌军阵脚溃散。每战出手不过数刻钟,敌阵崩溃,宋江兵马乘势突击,拿下敌城。破阵后他不参加杀敌,不收战利,退回本营闭门修道。
他从不参与忠义堂会议,不表态,不举荐,不派兵。他在梁山,不似将,不似谋臣,更不像兵卒。他是旁观者,是工具人,是雷电的操控者,是神鬼未现前最后一个替天出手的角色。他在梁山不居功不求名,只破敌阵,不杀一人。他的身影总是出现于军势僵持、敌阵奇诡的时刻。一现即退。
其他将领为名、为利、为忠义而战,唯他从不说“忠义”二字。他在梁山的存在是“非常规”的。他的力量被承认,他的人格被尊重,但他的心志始终未被收编。他接受招安,却不争职位;他领兵出战,却不管军政。他始终如临时借用的神符,一用即收,不留痕迹。
在梁山尚未正式受招安之时,公孙胜已三次归山。每次理由皆为“心志不定”“道法未成”“师命所召”。每次他归山,梁山战事吃紧,吴用亲去请人,他才再次出山。等战事一过,他又辞归。他不是战士,他是借住梁山的过客。他参战但不投身,他破敌但不执戈。
等到宋江正式掌权,梁山确定受招安,公孙胜未有明确反对,但态度极冷。他不参招安议,他不赴皇城领诏。他随军出征,但从不接官职。他没有像吴用那样入中书省,也未与李逵一同反对招安。他什么都没说。也不走,也不留。他在梁山,就是一抹云气,来无声,去无影。
梁山每打一次胜仗,将领皆得赏赐。宋江升官,卢俊义受封,吴用掌军务,李逵做提辖。公孙胜一直无职。最多被称为“随军道者”。这不是贬义,而是身份模糊。他不是将军,也非文臣,不为太监,不归佛门。他既不在朝廷系统,也不在军政体系。他是个借在梁山“搭便车”的修道人。他不抢功,不邀赏。他的唯一目标是:不违师命,不违天道。
他不忠于朝廷,也不忠于梁山。他忠于他自己的“道”。所以他未与晁盖同生死,也未与宋江共进退。他不参与天罡地煞的血誓,也未进入朝堂受封。公孙胜从来不是宋江的心腹,也不是梁山的核心。他只是梁山阵前的一枚“法牌”。不召不出,召则来破,破即归山。
征战未止,道心渐远招安之后,梁山人马分列官军序列,宋江为御前总指挥,卢俊义为副。吴用为军机参议,花荣统领弓营,李逵、阮氏三兄弟、秦明、林冲皆归属各部军团。唯有公孙胜,未编入任一营阵。他名义随军,实则不编军职,亦不居朝职。他与法术师乔道清并列,成为“辅助”官军之术士。
征辽之战,边境严寒,兵力分三路。北地风寒难御,辽军多用“风雷阵”扰军心。宋江兵困山口,请公孙胜助战。他出手一夜,引雷焚阵,辽军溃散。他只出一次手,之后不再露面。战毕即退,封赏也未受。
回师不久,田虎叛乱。朝廷命梁山系将征讨,宋江仍带公孙胜随军。田虎部中有术士施妖术于黄河两岸,驻军营地十日不得进。宋江再次请其破阵。公孙胜设坛一夜,清晨水雾尽散。军队开路,取田虎大营。他在前线只驻三日,破阵后即归营,不登前线,不插旗帜。
征王庆之战,敌军主将乔道清,善控五雷咒法,与公孙胜同出道门,互识根法。两阵对垒三日,法术交锋,雷声昼夜不息。乔道清败,投降。公孙胜不杀,不收,不押,只退入帐中,不言一字。此战后,宋江请他为“御前道官”,他辞。再请,仍辞。
他不是不想为国效力,也不是对朝廷怀有成见。他只是不认“名分”。道门中人,不争不斗,不入品级,不列班次。他认术不认将,信道不信君。他不是佛门清规之人,也不是兵家拜将之才。他是修道者,入世为破阵,出世为求道。他心中有一条“分界线”,世事不可久沾。
平定田虎、王庆之后,梁山人马伤亡严重,天罡地煞阵容凋零。昔日七十二将,死者过半。朝廷封赏,先后下达。卢俊义受封忠义侯,吴用得文散职,花荣任提督,关胜封副都督。唯独公孙胜,仍无官职。有人替他请封,他不赴京,他不受诏。他说师命未尽,不可久居人间。
朝廷不强逼,只赏赐绢帛、金银五十两,称“随征有功,准其归山修行”。他从不以此为辱,也不以为名。他退回蓟州,不再随军。宋江部尚需出征方腊,他未参加。宋江等人再无召他出山之语。吴用知其心志已定,不再劝留。
平淮归京,道士提出辞归淮西平定之后,宋江亲领梁山余部班师回朝。战后将士伤亡惨重,七十二地煞所剩无几。主将卢俊义、吴用、花荣尚在,副将大多阵亡。军中气氛压抑,胜而不喜。宋江回营整点将校,将功论赏,为入朝做准备。
营帐之外,春风乍起,旌旗不振。正当各部整队准备进京复命时,公孙胜向吴用传话,言辞沉静,请求觐见宋江。不是论功,也不是请赏。他说,有家事在身,愿辞官归隐。
宋江召见,他进帐陈述缘由。他不提战功,不讲劳苦,只说母亲年迈,无人奉养,自己久离山门,心道不宁,意志未定。言语寡淡,不诉不求。他讲完便退。宋江默然,未置可否。次日上疏朝廷,呈其辞行奏章。
朝廷批复迅速。赐金五十两、绢百匹,准其回蓟州侍母修行。未封官爵,未授敕命,仅书“随征有功,归山可也”。
公孙胜没有再入主将大营,也未再出席封赏仪典。第三日清晨,他整衣出营,只带随从两人、一卷经书、一口宝剑,未言告别,不辞将士。走时没有礼送,也无留人。
他离开的那天,没有战马,不见法坛。所有将校已各就其位,准备朝京城进发。宋江站在高台,望北方,不语。吴用低头入帐,未出言挽留。此后,他再未出现。
梁山最后一战——征方腊,他未参加。战后封赏亦无其名。宋江遇害,吴用自缢,他不在。李逵中毒,燕青归隐,他无声。
他不是拒绝朝廷,也不是抗命离营。他是“请辞”。请而得准,辞而不回。形式完整,过程合法,结局干净。他没有像鲁智深那样圆寂得道,也没有像林冲那样卧病不起。他没有被人害,也没有被人念。他就是不再来。
梁山死得多,活得少。活着的要么封官,要么罢官,要么落寞。公孙胜不是功臣,不是罪臣。他没有跟随大队人马迎接荣光,也没有陪着众兄弟走到尽头。他在整个梁山故事最喧嚣的时候选择离开。没有争执,没有异议。他走得安静。
二仙山闭门,道门中终老从梁山大营归去,他走了七日七夜,穿过官道,避开驿站,返回蓟州二仙山。山中罗真人仍在,道观冷清,庙宇苔痕。此地远离人世,不闻朝令,不达军报。
他未再出山。朝廷未召,他未请命。梁山旧部纷纷被调、被杀、被贬,他都未涉其中。他没有前来吊唁宋江,也未写信安抚吴用。忠义堂废,梁山被平,他不问。
他未再参与战事,也未接受敕令。他不是隐居,是彻底退出。他不是避世,是终止角色。他既不再是梁山的道士,也不是朝廷的臣属。他回到了他最初的地方,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山中道观。
山门常闭,香火不盛。他每日诵经、习法、侍母,无书信往来,无人造访。路人不识其名,道童不提其往事。他的名字从朝廷消失,从将册除名,从人心中褪去。
朝廷再未提他名字。忠义堂石碑上,写着阵亡将士与封赏名录,不含公孙胜。史官修《梁山功录》,略去其籍贯。官军清理梁山后裔时,无一人提起他的去向。他不在名单,也不在记忆里。
《水浒传》末尾用四字作结:“以终天年。”不提去世时间,不讲修道境界。不言荣辱,不写生平。他从入场到离开,从出阵到归山,从亮相到隐没,没有喧哗,没有波澜。他用一个离开的动作完成整部水浒的谢幕。
他不是最猛的,不是最忠的,不是最烈的。他不争位,不争名,不争理。他是那个最先离开的,也是最后活着的。他在故事最开始就来,最中间就退,最后也不回头。
他是梁山百将中配资老牌炒股配资门户,唯一一个全身而退,没有死,没有贬,没有官职,没有名字。他不是最精彩的,却是最完整的。
发布于:山东省倍选网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