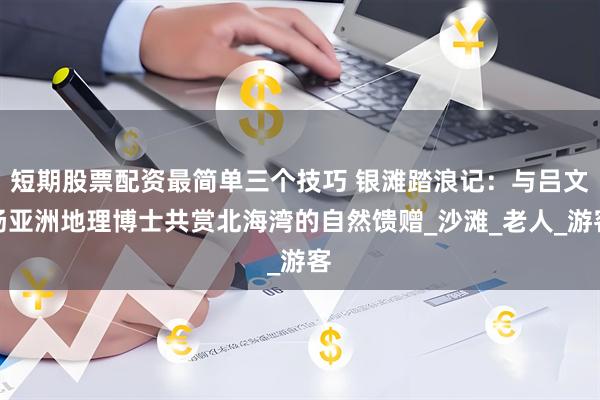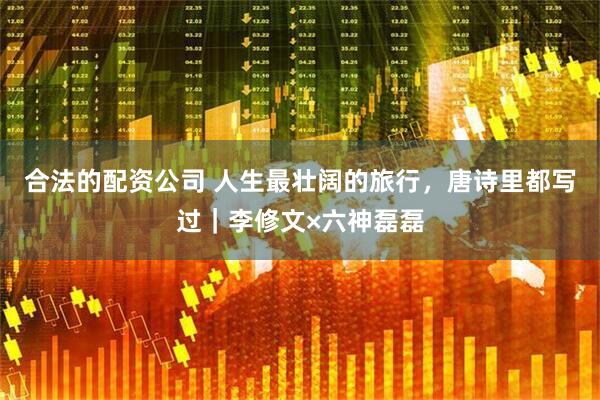
(图/《长安三万里》)
中国人都是唐诗的孩子。
从童蒙开始,随着一句悠远的“床前明月光”,一首天真无邪的《咏鹅》,唐诗就进入了我们的生命和记忆里。
在其后的人生中,也许我们放下了唐诗的阅读和朗诵,但它们总会回来,在“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刻,在“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旅途上,或是在“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的深夜里。
读唐诗,不仅仅是阅读唐人的生命,也是在走进我们自己的内心。“山川河流、清风明月、白云黄鹤、星辰渔火、名花幽草,在古诗中时隐时现,绘就出一幅丰富细腻的精神图卷。……它们绝非故纸堆里的粉尘、博物馆中的展品,而是流动的江河,至今奔涌不息,已经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生命血肉发生了无比深切的纠缠联系。”在清人蘅塘退士编选、作家李修文评注的《唐诗三百首》里,李修文这样写道。
展开剩余94%日前,新周刊邀请2025刀锋图书奖推委会主席、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和作家六神磊磊,在北京展开了一场题为“从唐诗到小说的文学壮游”的对谈。
两位对谈嘉宾与唐诗都深有渊源:李修文的最新小说集《夜雨寄北》,书名即来自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同名诗作,他今年评注的《唐诗三百首》、前些年的散文集《诗来见我》,都是读唐诗的过程中写成的;而六神磊磊从2022年开始创作“唐诗三部曲”,迄今已出版头两部(《唐诗寒武纪》《唐诗光明顶》),最后一部(《唐诗笑忘书》)也即将问世。
两位作家从唐朝文化热出发,讲述在今天如何重新发现唐诗,如何理解“壮游”和“壮阔之气”,现代人又如何在诗歌里看见自己。
✎采访 | 朱人奉
✎编辑 | 桃子酱
✎整理 | 张阿敏
李修文(图中)、六神磊磊(图左)、朱人奉在讲座现场。(图/新周刊)
壮游与弱游
朱人奉:或许我们可以从暑假游说起。近年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家喜欢到名人的墓园或故居去旅游,曹操、李白、杜甫、李煜等人的墓园成为网红景点。像高陵曹操墓前,有人送上布洛芬当祭品,还留下“愿天堂没有偏头疼”这样的祝福语,很有年轻人的特点。对此,两位老师怎么看?
李修文:我最近去了张居正的故居,“漫天风雪送一人”嘛。我看到,很多人也是给他送药,在他的牌位前摆了很多。我觉得挺好的,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呼应:为什么时隔多年,我们仍然觉得一个人和今天的人是有关系的?可能有一定的安慰、抚慰、满足。(去见他们)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网友见面——“奔现”,就是我看见的那个你,或者说我感受到的那个你,有可能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我写过一本书叫《诗来见我》,某种意义上也相当于给死去的诗人献上一份祭品。我是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的。你看他们墓前摆的那些东西,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弹幕一样。
昨天看了一条视频,用深沉的音乐配苏东坡的“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上面的弹幕一条一条的,其中有一条说“看来此人的才华在我之上”,确实让人忍俊不禁。很多时候,我觉得弹幕本身就是创作,就像给曹操和张居正送药一样,也是一种创作;很多时候,那些插科打诨可能才是我们时代真正的言说,我们在很多作品里看不到时代情绪,可时代情绪往往就诞生在给曹操和张居正送药的人里。另外,曹操也好,张居正也好,他们的确像镜子,能够让我们照见自身;还能够把他们生而为人的生机、趣味传达到今天,并且被我们感受到。这可能就是一种连接。我去一趟某个人的墓,我感受到了他走过的道路,他生命当中某一个攸关的时刻,并且我还愿意对此做个鬼脸,开个玩笑,发条弹幕,这是多好的连接啊。
六神磊磊:我想起来了,有点印象了。现在好多人去那些地方,是为了给孩子的中考、高考许愿。像白居易(朱人奉:还有王安石),因为是学霸、考霸,所以大家去跟他们许愿。我前一阵去保定莲池书院,那里有个“高芬阁”,寓意是得高分,去的家长特别多。有一年我去江油的李白读书堂,李白像前最多的,就是孩子的物理、化学等学科的课本、作业本,说明有这种实际的许愿的用处。但是许愿许到李白那儿,是选错人了。
李白与高适踏上壮游之路。(图/长安三万里)
朱人奉:访古是壮游的主要内容。两位老师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古代诗人是怎么开始壮游的?这些壮游经历又如何改变他们的文学风格?
六神磊磊:前不久,我刚从敦煌回来,到阳关实地看了一下。壮游改变诗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维。王维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如此温和、敦厚、宁静的诗人,但他出塞之后,却能写出那样雄壮、激烈的诗歌。我觉得,那是因为人走到远方之后,远方的山水、异域文化给他的诗歌注入了新的东西,会把他灵魂里更不一样的东西唤醒。
朱人奉:还有杜甫。但是他30岁之前的经历都没怎么写下来。
六神磊磊:杜甫年轻的时候有过那种壮游的经历、那种裘马轻狂的生活,就算他后边生活多么惨、境遇多么坎坷起伏,你感觉他胸膛里总有一个少年的、激昂的东西在流淌。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壮游对人的改变。
李修文:我们今天看起来的很多壮游,很有可能只是多少年以后我们总结的,因为他们成了特别伟大的诗人、文化符号。
我们是一个“诗教”民族,很多小孩是从熟悉诗歌,进而熟悉我们国家的伦理、规矩、尺度的——我们很多人的教育是通过诗歌完成的。就好像有个小孩到你面前,一般父母不会说“你给我们背一段孔孟”,肯定会说“你给我们背一段诗”。
因为我们是诗教民族,我们容易把一个诗人最后在文学史上完成的定位视作今天的认知前提。但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个误打误撞的产物,很多主动的、被动的遭际结合在一起,他才成为他。我们今天看起来的壮游,对诗人来讲,其实往往都是“弱游”。
那些大诗人刚出来的时候,像杜甫写“岱宗夫如何”,绝对是壮游。他在无比地渴望这个世界的壮阔,世界也因为他的踏足而变得阔大。包括苏东坡第一次出川的时候,那些诗就写得特别阔大。但是我们随后就会发现,他一生当中就不会再有那样充满了渴望或某种理想主义的旅行了,因为他大部分时候都走在被贬谪的路上。实际上,中国伟大的诗人,他们的名作都写于低处,而不是高处。
李白的晚年愈加失意。(图/《长安三万里》)
像李白这种,他是天外飞仙,是我们想象力或者日常生活的一个彼岸。他跟杜甫生活在同一个年代,但我们很难从他的诗里发现诸如安史之乱的影子,杜甫的诗里就比比皆是。所以,我觉得是个人的气质、遭际决定了这趟旅程到底是壮游还是弱游。我个人觉得,我更信赖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无数次弱游。
李白在黄鹤楼写“孤帆远影碧空尽”和“江城五月落梅花”的时候,一个在看着一个辽远的世界(“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一个是说我在这个楼里头画地为牢,一阵笛声响起,江城的五月也落起了梅花(“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当他把自己的处境、自己做的这一座囚笼当成整个世界的时候,世界变得很阔大,所以他这一趟行程可能也是一种壮游。我觉得它是相对的。
我是湖北人嘛,来自汉江边的江汉平原,再举一个杜甫的例子。他那首《江汉》有一句“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我就觉得很壮阔。杜甫这个人就像一个书记员,他记录着每一个普通人在日常当中的那种生活感受。他既像我们的父亲,也像我们的祖父,或者是我们的兄长——总之就像我们的家庭成员一样。他受过的苦,在苦当中所做的自我的弥合、心理建设,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
而且,他那种壮阔并不是说马上要奔向一个多么阔大的世界,还是在解决自身:我看见落日,心里仍然有那么一丝壮怀的东西,而我的病也有了治愈的可能。这是咫尺之内的壮阔,也可能才是值得我们信任的壮阔。
《长安三万里》里的黄鹤楼。
日常生活的壮游
朱人奉:在你们的生命中,有没有一次印象深刻的壮游经历?
六神磊磊:刚刚修文老师给了我一个启示。早年那些诗人离开家乡的时候,是气魄很大、想法很多的,但所谓壮游未必在文学上特别成功,往往是你所说的“弱游”或“穷游”,恰恰走成了人生的“壮游”,这个对我启发蛮大。
像王维,“使至塞上”,其实当时王维也是被排挤的。735年,王维在赋闲很久之后得到张九龄的赏识,有了重新回到中央做官的机会。但没多久,张九龄被贬逐,王维的靠山倒了,他被排挤出中央,才让他去劳军,等于是赶到一个偏远的地方。恰恰是他人生的这次穷游,才变成了文学上的壮游。
我走的地方少,我觉得我最“壮”的一次就是十几岁离开家乡去读大学。当时觉得自己气吞天地,有无限可能,是心气最高的时候。我从江西老家出发到北京,要先坐四五个小时的车到南昌,再从南昌坐18个小时火车到北京西站,然后倒两趟公交车到学校。我觉得那是我最少年心性的时候,后来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李修文:壮游,一种是地理上的壮游,另一种是日常生活的壮游。对我来讲,地理上的、让我今天都无法磨灭的壮游,是多年前的一次西北行。
那时候,我小说写不出来,去做了编剧。正好我要去一趟甘肃,就找了作家叶舟,“骗”了一个朋友的车。我俩穿越了整个河西走廊,一直到了德令哈,再从德令哈回青海。这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体验:我第一次去到戈壁滩,也第一次见识到了诗人岑参——他是我的老乡,也是湖北荆州人——所写过的那种景观。
我一直对他充满了好奇。像荆州这么一个充满了梅雨季、竹林、青石板等南方事物的地方,要明心见性地把飞沙走石、辕门飞雪这些东西一点一点描述出来,可能非常艰难。那次我一边往前走,一边好像理解了岑参笔下的那个东西。很多时候,他已经不比喻了,就是名词接一个名词,他只需要把每一个名词写出来。
一旦真的活在了我们想象过的处境里,我们作为连接者、处理者的身份就被取消了,你就是一个看见了周边世界的人,你就是一个转述者,你把你看见的东西表达出来,把它一字一字地写出来,就可以了。
包括刚刚说的阳关,我也去过。正是在那一趟旅程当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大漠孤烟直”。那个东西,确实不单单是说龙卷风起来的时候连风柱的形状都是直的,你靠一种美学上的想象力是没有办法把它想清楚的。所以,我觉得壮游其实是格物,没有那么多凌空蹈虚的东西,就是拿你自己的肉身、拿你的感官和体验,真正地重新见识一些名物、认识一些词汇。有的时候我们走得再远、踏破河山,可能只是为了认清一些植物、一些沙石、一些山川的名字。
但在唐诗里,我更珍惜另一种壮游,就是日常生活的壮游——我如何和我自己的生活、我在生活里的破碎和解,如何真正踏上一条通往我理想中的生活的道路。很有可能,这种生活是失败的。
作家李修文。(图/新周刊)
朱人奉:是不是杜甫在成都建草堂的时候?
李修文:我觉得也不是。那是他的一个避风港、一个生活中的情境、一个太虚幻境,暂时庇佑了他;是他离开四川以后不断怀念、不断追忆的一段时光。
有一个人特别典型,就是我很喜欢的韦应物。他把日常生活当作那种险峻的、我们想征服的河山,当然可能他也不自知。像李白,他在这座山或那座山留下了圣迹,而韦应物在锅碗瓢盆里留下了圣迹。每一件用具,对他来讲都是一座山川、一条河流。他在对日常生活的消化当中,完成了一场壮游。
他写“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表达的是一种巨大的原谅——原谅了世界,也原谅了自己:无论是“春潮带雨”还是“野渡无人”,我这艘小船就像苏东坡讲的“不系之舟”,随意而流。就好像他真的跨过了山峰,完成了一场壮游。壮游可能并不是不断进取,不断前进,不断去往一个我们未曾到达的世界,而是回过头来,在咫尺之内把锅碗瓢盆当成必须经历、必须跨过去的山峰。这样一场壮游,更加让人确信。
朱人奉:修文老师在评注《唐诗三百首》时提出,“春潮带雨晚来急”这句诗代表了人的一个最高境界。为什么这么说?
李修文:对。我们今天谈论的所有诗人,都特别复杂。苏东坡写“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好像他到黄州来就是为了他的天命,就是为了完成这首诗的。其实不然。
苏东坡全集里有很多文字写到他在黄州的生活。他那时最受困扰的问题是什么?至少有一桩是怎么种田。他不知道怎么种,只能不断请教别人,然后一次又一次地露破绽。好多人都说,你看,来了一个不知人间烟火的人。可这就是他每天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完成的壮游。他把这亩田耕好了,属于此时此刻的这一场壮游就完成了。
苏东坡每一次被贬谪,包括被发配到海南,我们之所以觉得他的经历是壮阔的,并不是他战无不胜,而是他在面临如此大的灾难的时候,他还有能力成为一个正常的、平静的人。你想他60多岁发配到海南,肯定是有去无回。但他仍然在路上等着他弟弟,作为一个人完成作为一个兄长的本分。那种壮阔,并不是因为你是天外飞仙,而是你来自我们中间,你没有背叛我们,最终,你的人生、你的作品完成了,帮我们建构了面对日常生活的勇气。
他从海南回来,再次翻越大庾岭,遇到同一个老翁,问人家“曾见南迁几个回”:那么多贬谪到海南的人,像我一样活着回来的,你见到过几个?我还是可以的吧?遭受了如此苦厄,他仍然破绽百出,仍然一得意就忘形,不断地赞美着自己的侥幸或者说是生命力。就是那种真正的生命底色,让他完成了某种壮阔之气。
一个人,不是变成你想象的对象之后,生命因此壮阔;而是无论你遭受多少风浪,我们仍然相信你是一个生活意义上的人,并且你的存在能够鼓励我的存在,这才算是真正诞生了某种值得信任的壮阔之气。
朱人奉:六神老师觉得哪个诗人具备这种“壮阔之气”?
六神磊磊:我想到修文老师的一位湖北老乡,孟浩然。他一辈子几乎都待在襄阳,没怎么壮游过。“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他觉得还是家乡最好。有时候壮游也不是说要去多少地方打卡,而是要找到自己活着的真正意义和使命。
孟浩然也曾出去应试。他求取功名的时候,那种热切是写在纸上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渴望像大家一样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后来发现那不是自己内心的声音的时候,他回到了故乡,再也没有出去。你看孟浩然晚期的诗,内心平静,无比自洽,我觉得他是真正完成了人生的壮游。
很多唐朝诗人写田园诗,你会觉得他们是田园的客人,包括王维的诗,就是“我来了,我看了,我走了”;但是你读孟浩然的诗,他写的是“我就是这里的一分子,这田间就是我生活的地方”。他悄然完成了人生的壮游。他自己定义了失败,他和其他唐朝诗人活得都不一样。
李修文:和去长安相比,孟浩然回乡才是真正的壮游。他在当时已经启发了很多人,那就是除了不断的进取,还有另一条路:不卷了,回家。
作家六神磊磊。(图/新周刊)
唐诗与《聊斋志异》
朱人奉:我有一个感觉,喜欢读唐诗的人常常会因为一首诗或一句诗去一个地方。学者赖瑞和因为那句“五城何迢迢”,只身寻找盛唐留下的遗迹,写了一本《杜甫的五城》;最近热播的《长安的荔枝》,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所阐发的故事;而修文老师的小说集《夜雨寄北》,跟李商隐的诗同名。想请教一下修文老师,为什么以这首诗作为由头或者一个线索?
李修文:中国有个成语叫“心猿意马”。当我们要生活、要往下狂奔的时候,往往像那匹狂奔的马,可是我们的身体里老是躲藏着需要我们去周旋、去对峙、去相处、去驯服,有可能也驯服不了的那只猿猴。某种程度上,我写的是一个人和自己的心魔相处的过程。
为什么用这首诗?我觉得,诗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有句话叫“以诗证史”,往往在历史里找不到的东西,我们要到诗里去找。
我们其实很难和我们经过的年代、历史告别。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抽身告别心魔、告别那个年代的时候,实际上它到今天为止还在作用着你。有时候是历史,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两句诗,那个诗就是我们的出身、我们的渊源。所以,我想用这两句诗代表我们过去生活的某一段过往、某一段历史,甚至某一段梦魇。倒真的不是写一个爱情故事。
朱人奉:修文老师的小说写的是一个女生跟婆罗洲的一只猴子之间的故事,这只猴子后来学会背《夜雨寄北》。
六神磊磊:《夜雨寄北》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故事。一方面,它来自传统文学。中国文学里有把猴子当人写这么一种传统,在《聊斋志异》里有很多类似的故事。金庸先生的小说里,也特意写了中国武功的源头出自一只猴子。另一方面,在这篇小说中,你会看到其他作家的样式和风格,比如川端康成的《禽兽》。
猴子是小说的主角,它会说人话,会疯狂地报复女主角。但如果把猴子整个拿掉——这是我瞎想的,故事仍然成立。这只猴子就像修文老师说的女主角的“心魔”。女主角的男友人不错,但他穷,没有出息。猴子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男的从你身边赶走,他不配你,我要占有你。其实,这可以视作这个女生内心的声音。我要向上走,要追求别的东西,要把这个男的从生命中赶出去,但我自己不愿面对,就委过于一只心里的猴子。
这篇小说非常有意思。它既是魔幻的、脱离现实的,但又好像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一个人人生破碎的故事。我特别喜欢书中的一句话:“大家也就各奔东西了。”我觉得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各奔东西”,人生就是不停地在一个又一个地方各奔东西。
修文老师写的那只猴子,用一种刀割一样的声音吟诵“君问归期未有期”,不停地问主人公:你的归宿在哪里?你的灵魂在哪里?你的初心呢?修文老师可能觉得《夜雨寄北》特别切合这个主题。
《夜雨寄北》
李修文 著
花城出版社,2025-4
朱人奉:这篇小说确实有一种《聊斋志异》的感觉。修文老师也提到,自己的一些创作灵感或者说观念来自《聊斋志异》。一边读唐诗,一边读《聊斋志异》,修文老师从中读到了什么共同的东西?
李修文:顾随先生说,写诗、写作是“不得已”,而不是“得已而不已”。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他不服于传统那一套解说系统,经常化名为“异史氏”,通过他的美学、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解释他对这个世界的运转规律的理解。我感觉,这对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三个字——不得已。
我如果不写,就不能度过此时此刻。就像蒲松龄,如果他不写,就会像他笔下那些无力的书生那样。他从来没有写过那种完美的、对天下道义负有责任的、特别正人君子的书生。他笔下的书生,动不动就被勾引,那么脆弱:妖狐野怪怎么就那么容易摄你的魂?你怎么就那么容易晚上跑到荒郊野外?说明你六心不定。
我想说,某种程度上《聊斋志异》是一本自传。那些书生,可以理解为一个个活在世界上,乱了方寸、不由自主,没有多少控制力也谈不上什么纪律的人。我的一生并没有获得什么,我的理想无法在朝堂、在那种广阔的地方实现,反而在荒郊野外、荒废古寺(实现了)——妖狐野怪可以理解为书生心目中理想化的自我,就是出于现实的匮乏,所渴望的另一个自己。
蒲松龄伟大的地方在于,他让那些走投无路的人有地方可去。在现实里找不到的归宿,可能阴曹地府里有。他也像个导游,引领我们去看待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生活是一片废墟,废墟之上长出了狐狸、长出了妖魔鬼怪,但我们的生活仍然充满了奇迹,如此值得一过。
六神磊磊:有人说《红楼梦》像秘境——“琉璃秘境”,李商隐的诗歌、蒲松龄的谈狐说鬼,都是秘境,他们用一套玄妙的、难拆难解的东西来表达自己。
诗歌,就像在历史的山峰中穿过的河流,历史长成什么样,诗歌就会被塑造成什么样。有时河面比较开阔,比如7世纪末期到8世纪上半叶,诗歌就比较开阔,“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但到了李商隐那个时代,河流变得蜿蜒曲折,李商隐必须表达得非常小心、幽微,这可能也是一种“不得已”。蒲松龄也一样。
《诗来见我》
李修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3
朱人奉:修文老师写过一本散文集叫《诗来见我》,我读的时候能感受到有一种浩荡、淋漓的江湖气,好像我们的一些情感、命运、遭遇都被写下来了,就等着哪一天去把它翻开。
李修文:这本书是在当年的疫情中写完的。疫情刚开始时,我跟一个朋友打电话,说:“家里没吃的,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后来,能出门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从朋友那里拿了两捆青菜、一捆豆皮儿回家,但我其实很久没见过这个朋友了,所以,回家的路上特别有感触,想起了杜甫的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我觉得我就活在杜甫写到的那些处境当中。我们可能逃得过李白对我们的指认,但逃不过杜甫的指认。他总有一句诗,在等待着见证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或某一个时刻。
为什么书名叫“诗来见我”?“见”就是“现”,我要在诗歌里看见自己,每一个肉身都要在那些伟大的诗句里现出自己的本来面目。而各种各样的我,早就被各种各样的诗句见证过。所以,在相当程度上,我写这样一本书是为了安抚自身,在那段特殊的时期里,我要让我自己好过一点。
王晓磊(六神磊磊)的唐诗三部曲已出了两部。
六神磊磊:我现在41岁,已经有了“访旧半为鬼”的感受。有一次,在深圳,我们几个同学见面,我问“曾勇怎么没来”,他是我同桌。结果那天才知道,他过世了。所以,还是杜甫厉害,每次聊唐诗聊到最后,杜甫就会出来。
诗歌、文学是什么?就像前人走过了荒野合法的配资公司,埋了一块路碑;也许它已经被荆棘、蒿草掩盖,但你扒开草丛,看到这块碑,就知道前人来过了。
发布于:广东省倍选网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